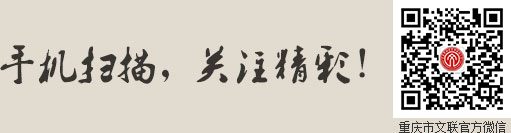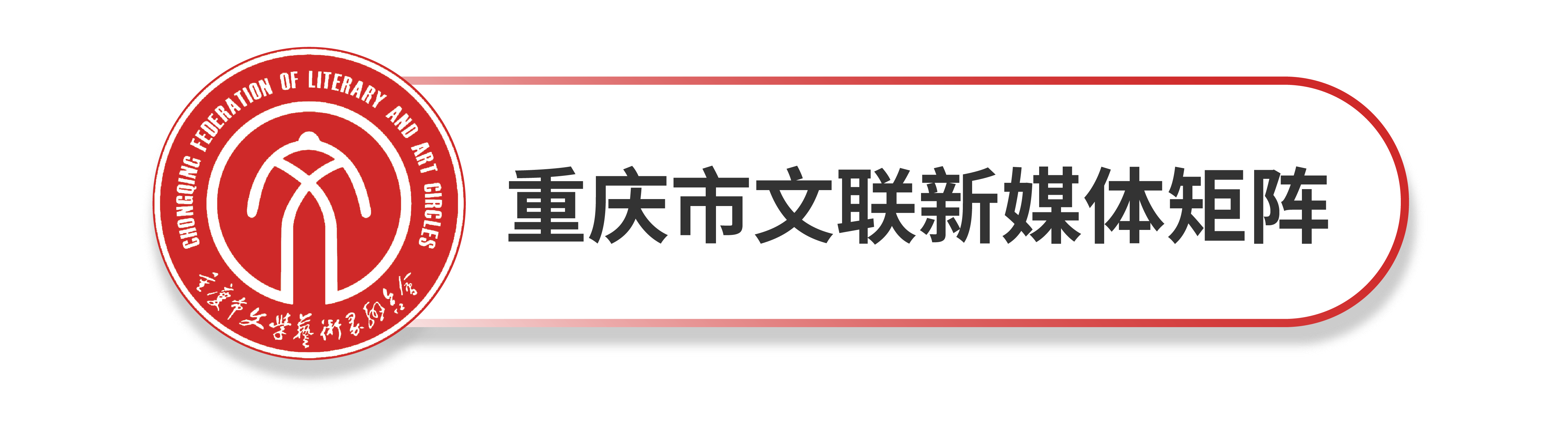观点(选自《重庆文艺》2022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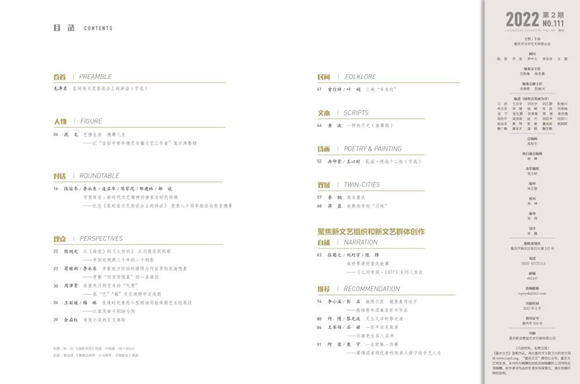
# 《重庆文艺》2022年第2期内页
多重地方经验的接续与何其芳的成渝想象
——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
文 / 苟健朔 李永东
学界往往将何其芳写作《梦中道路》或奔赴延安作为其思想转变的“界石”,所涉及的时间点是1936年和1938年。两种“界石”指向两类对象。1936年,何其芳开始厌弃“自己的精致”,从此“要叽叽喳喳发议论”,由此诞生的,是从“梦幻”中醒来的“现实何其芳”。而1938年,也确是把他“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但这里的分裂对象,则演化为“为文学”的何其芳与“为政治”的何其芳。何其芳并非直接由“北京化”突转为“延安化”,还有三年内多种地方经验的加工,“抗战爆发而辗转重庆、成都等地时遭遇的种种人事纠葛和内地闭塞的环境的冲击,显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三年的距离与地方的转移,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场域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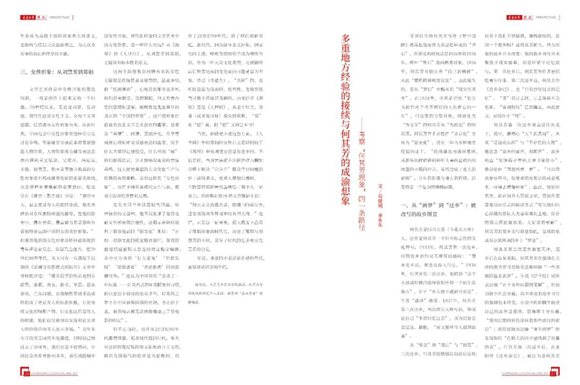
# 《重庆文艺》2022年第2期内页
一、从“画梦”到“还乡”:被改写的故乡图景
何其芳是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人,还乡是何其芳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1933年,何其芳第一次还乡,回到北平后给吴天墀写信感叹:“重来北平后,常念及故人行止。”1936年,何其芳第二次还乡,却抱怨“这个小县城对我冷淡得犹如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于“乡人便不感到可亲近”,生发“凄凉”感受。1937年,何其芳第三次还乡,再次给吴天墀写信,他谈论自己“不常回忆过去”,因为旧景总是辽远、朦胧,“而又那样令人感到寂寞”。
从“常念”到“凄凉”与“寂寞”,三次还乡,何其芳的情感认知前后反转,以至于我们不禁疑惑,他所描绘的,是同一个故乡吗?就何其芳而言,作为对象的故乡并未改变:他的故乡书写并未聚焦于现实描摹,而是钟情于记忆叙写。第一次还乡后,何其芳所作多是描绘童年往事。第二次还乡后,何其芳作《还乡杂记》,也“只有抄写过去的记忆”。“景”是过去时,过去体验不会更新,“客观特质”已然确定,由此而言,症结在于“情”。
何其芳第一次还乡前后居住在北平,此时,他动心“人生的表现”,喜欢“辽远的东西”与“不存在的人物”。他思念“故乡的雷声,和雨声”,故乡的山“装饰得童年的天地非常狭小”,他却依旧“真想再看一看”。“可以借助象征符号,接受者的反复训练或重视某一环境去增强形象”,由此,谈论何其芳,就必须介入京派文学。京派作家喜爱以回忆式的叙述方式“写出他们内心深藏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土地,保存的那点原始自然美、人情美的光影”,何其芳的故乡书写即是如此,呈现的是具有京派风味的乡土“梦景”。
何其芳第二次还乡前在天津,还乡后在山东莱阳,何其芳多次强调在天津的教书岁月使他无法继续做“一些美丽的温柔的梦”。小说《浮世绘》试图表达他“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但依旧缺少社会容量。其中涉及的故乡书写的情调也未转变。小说中的应麟生叙述自己的故乡是匪国,恐怖却十分有趣,“他用幻想的彩色涂抹着那些恶汉的面目”;欧阳延陵也比喻“童年的梦”的发现如同“在秋天的园子里找到了迟暮的花”。何其芳第二次返乡后,在莱阳作《还乡杂记》,被认为是何其芳思想转变的“界石”,标志着何其芳由“‘刻意’‘画梦’开始面向现实”,转向人生。谢慧英强调:“对何其芳来说,‘地理还乡’的强烈失落感预示着他‘精神还乡’的心理吁求和自我蜕变的强烈冲动。”可吊诡的是,何其芳的《还乡杂记》多是“抄写过去的记忆”。既然没有“新”事物产生,“失落”又从何说起?实际上,何其芳在讲述《还乡杂记》的写作计划时,谈论的全是莱阳感触,何其芳感叹“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是他发现的“精神上的新大陆”。
试想,如果我们跳出“还乡”一词的限定,而只是将其看作一种修饰,会发现其体现出何其芳思想观念的转向,而转向的动机,就是莱阳体验。所以,在《还乡杂记》中,不仅“有趣的”“匪国”转而使人“沉重”与“低抑”,“美丽的乡土”变为“阴暗的,汙秽的,悲惨的地狱”。这些,正与莱阳经验相对应。
在《呜咽的扬子江》中,何其芳乘船反渝,同行者都称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他却将其比作“狭的笼”。对比天津时的故乡想象也可看出,何其芳是以事后总结的态度来概括返乡见闻,而当时的情感自然被修改。海登·怀特强调:“经验世界是以两种模式存在:一个编码为‘真实’,另一个在叙事过程中被揭示为‘虚幻’。”何其芳正是以莱阳经验唤醒故乡的隐藏记忆,编码“真实”。这也难怪于何其芳陆续写着、读着《还乡杂记》会感到“惊讶”,感叹自己的情感粗糙起来是“意料之外”的。
二、成渝体验与孤独的深化
何其芳后来反思《还乡杂记》时说尽管自己宣言最关心“人间的事情”,但“仍然最关心的是我自己”。可以看出,在《还乡杂记》中,何其芳的故乡想象有两个特征。第一,排列出故乡的各类问题,却“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还未找到明确的道路,还带着浓厚的悲观气息和许多错误的思想”。第二,依旧“藏在厚厚的个人主义的外套里”,只是在现实中有“不同的实践分野”。何其芳在回答中国青年社提出的“你怎样来到延安的?”问题时,总结自己“是孤独地走了来”。孤独是何其芳战时成渝体验(赴延安以前)的核心情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实际上,当何其芳以成渝经验审视成渝时,正是通过不断“疏离”,才促使其在现实道路上不断深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何其芳返回万县,此时的孤独体验,第一层来源于学校。何其芳是万县师范的一名教师,相较于莱阳学生们“热心地追求着知识和进步的思想”,万县学生的精神上却多“看出‘绝望’的表示”,“丧失了理想”。在学校,有理想的学生甚至会被先生认为“有点神经病”。此外,教员们“成天打着麻将”,“关系他们的职业和薪金更甚于关心抗战”,这与何其芳的思想诉求格格不入。第二层来源于当局的限制。在万县,何其芳还是《川东文艺》的编辑。然而,在沉寂的万县,进步刊物的运营却屡屡碰壁,不足数月,《川东文艺》便被当局查封,何其芳也被通缉。
1938年,何其芳来到成都,他同样因与此地守旧、懒散的地方风气格格不入而备感孤独。这时的成都“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象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在“故纸气”的氛围下,人民生活变得“很少有振作的朝气”。何其芳曾撰写《论本位文化》《救救孩子》等文对此现象进行批判。另外,何其芳创办抗战刊物《工作》,“全心全意转入抗战工作和革命工作”,然而成都的社会风气是慵懒与享乐的,这在他的《论工作》《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中得到充分展现。
此外,他在成都还新增了一重孤独——被京派同仁疏远。周作人附逆后,何其芳撰文《论周作人事件》予以响应,在他看来,周作人的附逆并非“偶然的失足”或“奇突的变节”,而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结果”。然而,关于周作人是否附逆,“当时文化知识界有些人还抱观望怀疑的态度或者怀有惋惜的心情”。《论周作人事件》一文受到同仁们的质疑与否定,好友也疏远了他。朱光潜不仅认为周作人没有附逆的野心与勇气,也嘲讽了何其芳攻击周作人私生活的不当行为,强调私生活“不应和他是否附逆相提并论”。成都同仁们的疏离与批评对何其芳打击尤深,促使何其芳的孤独体验达到顶点。
正如黄伯思所言,何其芳“走出了象牙之塔而漫步向十字街头。塔里的人向他挥手惜别而街上的人熙来攘往,还没有太多人来迎接他,在这儿,我们的诗人还有一段寂寞的旅途”。由此,何其芳眼中的成都,只能是“古老”与“寂寞”,逃离成都,是他必然的人生道路。
三、延安经验与作为“他者”的成渝想象
张英进认为描写小镇有四种样式:牧歌的、哀怜的、幻想的与讽刺的。《画梦录》中的故乡正好对位“牧歌”样式,而《还乡杂记》的成渝两地书写,也与“哀怜”样式相匹配。不过,随着孤独感的深化,何其芳的成渝想象又向“讽刺”模式转变。
1938年8月,何其芳来到延安,孤独体验随之消失,体现在诗歌形式上,是个体到群体的叙事转变。在《夜歌》中,何其芳就多次使用“我们”作为叙事主体。在他的行文态度上,“我们”的组成与联结,不在于地理坐标的远近与交往沟通的疏密,而在于思想情感的共鸣,通过共鸣,可以达到“我们虽还不认识,/我们已经是同志啦”的叙事可能。较之成渝的压抑,延安首先具有无穷的包容性,“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又“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其次,延安体现着进步,较之“死城”成都,延安在“不断地生长”。最后,较之孤独的成渝体验,延安体验是幸福的,这里有着“自由的”与“快活的”空气,“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段从学认为《画梦录》所营造的精致冶艳的唯美世界映射的是何其芳对现实世界的厌倦。“精神故乡”的生成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厌倦,而回归现实的何其芳,又以“牧歌”故乡内含的精神高度来考察成渝两地。然而,成渝两地的孤独体验促使何其芳重寻新的“精神故乡”,延安便成了精神寄寓的对象。所以,何其芳才会感叹延安是他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他就像生活在“那种想象里”,所以,延安形象的建构处处在填充成渝两地的空白。此外,延安的发现,还促使他在城市想象中融入政党理念。延安时期,何其芳的《饥饿》再续成都想象,构型了两幅场景。一幅是穿着中式衣装的男子或打扮得像姨太太的女子在茶馆、射箭场休闲娱乐,另一幅则描绘何其芳购买的糖糕不小心掉在地上,一个小女孩突然弯腰拾捡,放进嘴里,又迅速离开。何其芳构型的两幅场景形成反差,他“直觉地讨厌”前者,而称后者为“庄严的景象”。何其芳慨叹“和平的城,有着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这早晨的静寂的白色的光辉中你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经窥见了的一个可怕的秘密”,于此,成都成为旧世界的象征。其次,是成都的政党化。在文中,何其芳分类自己的梦,发现有两类新梦,“一种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是饥饿性的”,在他的思想观念里,两种梦具有因果关系。何其芳以新梦修饰旧主题,成都成为延安的“他者”被重新想象。
相比成都,何其芳笔下的陪都重庆具有更典型的政党意义。何其芳称赞延安为“革命的心脏”,批判重庆“乌烟瘴气”。在他眼中,重庆与日寇汉奸都是旧世界的表征,应被消除。描绘重庆严重的阶级对立图景在《北中国在燃烧》《重庆街头所见》等文中随处可见,是何其芳运用政党意识进行重庆想象的主要策略。除此之外,何其芳也直接批判国民政府。显而易见,何其芳将“国家”形象化并融入城市想象中,当以“国家”照耀重庆时,重庆显然失责。
总体而言,具有延安体验的何其芳对于成渝的想象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何其芳作为“超然的叙事者”,与成渝两城“保持距离”,正符合“讽刺的”城市模式建构。
四、结语
“何其芳现象”其实“蕴含着中国现代性结构的内在分裂与冲突”,透过它,可以看取战时知识分子的群体心灵辙印图。当然,“对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是借助于公共空间才能完成的”,而城市是最佳对象。何其芳笔下的成渝形象是多重地方经验彼此接续的混合想象体,它既容纳了多个城市的话语力量,也作为何其芳转向的形象修辞而存在。由此,探讨何其芳的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是将抽象问题具象化,将作家论与城市形象问题转化为文化史与认识论的问题,发现战时中国的丰富与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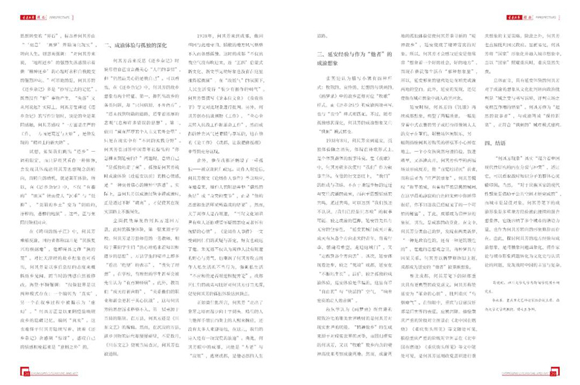
# 《重庆文艺》2022年第2期内页
苟健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永东,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