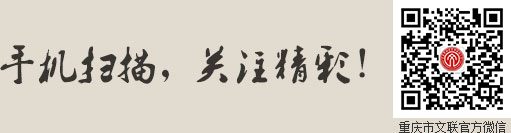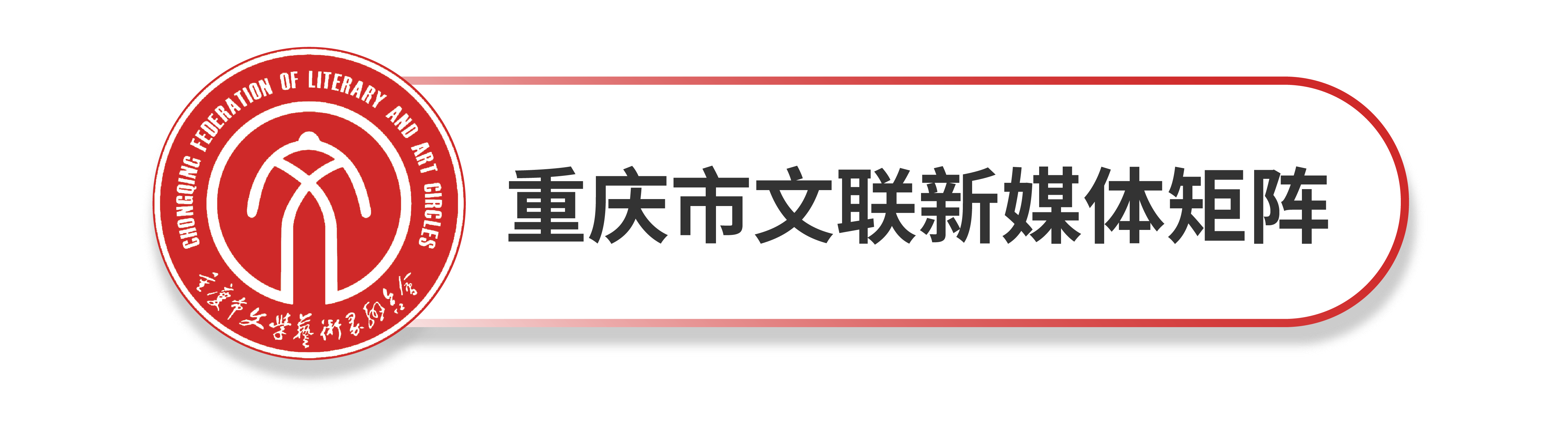新时代以来重庆音乐的发展策略与标识底线
文/林弥忠 于昊旻
新时代以来,重庆音乐通过流行音乐、民间音乐及城市音乐等的征用与修辞,建构出具有情景内涵的声音景观,在以城市文化为底色的音乐叙事中,兼顾时代性、创新性、跨界融合等媒介特质,借助声景迁移在艺术市场、民众接受等方面形成价值传递、情感共鸣与精神共振。重庆音乐的创新发展由多重原因推动而成,如作品的话语空间与生成机制、音乐本体的审美价值与语言叙事、受众群体的审美认知与接受语境等。近期,重庆对舞台艺术“渝韵”计划的实施,为新时代重庆音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为此,凝聚时代、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诉求,以创新性叙事语言及美学内涵讲述中国故事、重庆故事,激发受众群建构起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联的主体性意识,成为当下重庆音乐界的努力方向。
一、重庆音乐的人民底色及经典样态
从现存史料及作品流传程度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等影响,在一系列“改造”与转换下,“人民”属性贯穿音乐创作,至今仍作为音乐实践的既有尺规与支点,对新时代重庆音乐尤其是经典音乐实践进行建构。可以说,对人民的关注或作品中所传递关于国家、时代、民众的通约性思考成为不同时期重庆音乐的共同点,也是经典得以产生的现实依据与逻辑起点。
一方面,这与重庆曾为战时首都的历史底色有关。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有作品发表或创作的作曲家有60余人。如陈田鹤在8年中创作了46首作品,占其作品总量的1/5。更创作出了以“五三”“五四”大轰炸为故事基底的钢琴曲《血债》,是我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题材钢琴曲。此外,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重庆新音乐运动蓬勃发展,“一刊一社”(《新音乐》与新音乐社)相继创立,与大众革命运动相结合成为刊物的创办特点。该刊物使用较多板块推介解放区的革命歌曲,如《黄河大合唱》等寄托国民救亡图存热情的作品,所传递出的生生不息、坚强不屈的民族气魄与战时重庆的广大民众形成共情。这种对基于共同民族记忆、立足国家叙事原则作品的推广与传唱,为重庆音乐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今年,由梁芒谱词的流行音乐《龙》登上央视春晚,歌词“今天我们都是龙……不同的心跳连成了五千年的梦”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底蕴和中华儿女的共通情感相呼应。此外,他为电影《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所作的主题曲《兄弟》《23秒23年》,叙境音乐与影像的整合建构出特定时空下的大事件,音乐为影像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增强了受众对解放战争、唐山大地震的民族记忆,协助剧情及人物塑造完成了对中国人民有特殊记忆的重大事件的整体化编码与情感传递。
可以说,“人民性”始终与中国革命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相连。既指向时代变迁,亦与民族国家叙事相关联,更多的关注作为集体的民众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命运走向,作为“我”的个体指涉则被隐于国家民族的话语叙事之中。如今年举办的“百花齐放庆华诞”——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主题音乐会,以管弦乐、交响乐等演奏形式系统回顾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阶段的建设成果。
进入新时代以来,《梦圆小康》主题原创歌曲交响音乐会、“金钟之星”“童声同乐”音乐会等活动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宏大叙事出发观照与叙述中国的当下发展,通过内容编排、视听修辞等音乐叙事功能创造出符合时代议题的声音景观。民族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以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基础,以重庆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夔门雄起白帝来……保三峡大坝无淤塞!”的传唱,在重庆方言、重庆音乐元素、啰儿调等传统音源与花腔女高音等现代歌剧之间捕捉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定位。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也就是说,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延展的“人民”定义,现如今要求真切捕捉人民群众打从心底的“喜闻乐见”。换而言之就是“既有生活底蕴又有艺术高度,要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而非“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二胡演奏者刘光宇是“舞台出真知”的代表,他始终在思考艺术创作与表演如何实现大写的“通”、广义的“俗”以及此过程“化”,对“二胡戏剧化”作出一定探索。他所创作的《蚂蚁》以童谣《黄丝蚂蚂》为基底,将渝人乐观火辣的性格注入小小蚂蚁上,民间音乐风格将艺术的“典型性变为普遍性”。由他带领重庆歌剧院所创作的《一江清水向东流》《尘埃落定》《红岩村》三部作品更是入选文旅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项目,通过音乐的具体实践为树立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高质量铺垫。
二、围绕地域性的讨论与重庆音乐的跨界实践
依托智能化时代技术变革的发生,作为声景主体的音乐逐渐溢出纯听觉媒介,转化为杂技剧、影视剧、短视频等的背景音乐,实现“视听微叙事‘麻醉式’传播的‘联觉’机制”。在这里,音乐作为凝结独特地域文化的声音符码,能够引起受众群体对特定时空环境、特定人物乃至事件的联想,由此传递出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此外,这种超听觉的多重感官体验对剧情类作品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纯音乐属性的声景向其他媒介形态的扩散与跃迁。
如重庆杂技艺术团打造的红色杂技剧《一双绣花鞋》采用了《黄杨扁担》《川江号子》等颇具巴渝特色的音乐素材,带有地域指向的声音元素象征文化身份,在深挖重庆人文底蕴来对演出进行视觉创新的同时,增强观众知觉体验与共鸣,从而产生情感体验与文化认同。还有以抗击“8.21”缙云山山火为话题产生的众多音频与短视频,如《重庆得行》中抗击山火的志愿者、消防员以平凡之躯对抗山火的片段搭配重庆方言Rap,不仅符合短视频行业地域下沉这一趋势,更显示出对特定地域及文化阶层的关注。作为渝都特有语言,重庆方言Rap的使用显示出“巴别塔效应”,在风格各异、类型多元的短视频文本中脱颖而出。
作为封存感觉、调动情感潜能的中介,音乐区别于触觉、视觉等可碎片化或选择性接收功能,具有在其他感官被封存的状态下,仅靠听觉也可摄取受众更多的感知力。去年举办的“歌唱新时代”重庆主题歌曲征集活动推出11件集聚重庆辨识度的原创歌曲,由陈刚创作的《新重庆跑起来》中的“把朝天门的大门徐徐打开”是对2023年春节期间重庆两江交汇处的烟花秀的词语想象。除歌词对重庆的地域定位外,在巴渝独特地域环境、历史民俗影响下所形成的多元音乐形式,既有高亢激昂的劳动号子,亦有悠扬婉转的山歌小调,极具特色的民间音乐声景建构起听众对重庆的想象,使其感知音乐所蕴含的美学信息、地域信息及文化记忆等,从而增加外界对重庆的认识并产生“数字地方感”(Digital Senseof Place)。此外,以大型原创交响乐《重庆组曲》为代表的城市音乐(该类别发轫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建设潮流中),是当代极具城市符号的音乐类型之一。该作品从历史、文学与自然三角度出发,《钓鱼城》《解放碑》等构筑了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民族之魂;《白帝城》《竹枝词》书写了城市的文化底色;象征历史遗迹的《朝天门》等赋予了城市人文内涵;以市树黄葛树为对象的《黄桷树》则传递重庆的自然风韵。基于巴渝风俗,汲取民间音乐素材,在交响乐、打击乐与民族乐器等多种器乐、声乐元素的整合下,生成重庆的历史与当下。这些作品既走出了传统音乐的实践困境,又结合城市自身的发展与现实,将“地标音乐”与“个人风格”完美糅合。
此外,音乐剧作为外来舞台艺术(20世纪80年代引进),历经原本引进、编译中文版、尝试创作原创作品等阶段,已成为当下音乐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由冯柏铭、冯必烈父子根据作家阿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民族歌剧《尘埃落定》荣获“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这是重庆在音乐舞台戏剧的一大突破。该剧2018年12月首演以来,此剧已在全国各地演出70余场,彻底突破了原著的思想困囿,在“承”与“变”中找准了最佳契合点,运用对唱、独唱、重唱、合唱,加之富有藏族风格的音乐,在强化戏剧张力的同时,尽显歌剧媒介魅力。
除对原创剧目的执着追求外,对经典文本的再演绎也是今年重庆音乐界的努力方向。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的不断演进中,音乐领域也呈现出混合媒介、多维体验等表演形态的拓展。基于此,重庆音乐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跨域跨界协作的主动意识与实践指向。于去年年底以意大利原文演绎的威尔第世界经典歌剧《茶花女》,在舞台布景上大胆突破,将隐匿于传统乐池的乐队可见于舞台后侧,沉浸式表演加强了舞台的戏剧效果;即时的背景乐曲外化人物角色的心理活动,如薇奥列塔面对爱与不爱选择的紧张时刻,强烈且极具动感的音乐极大加强了戏剧的张力与人物间的戏剧冲突。借助灯光投影对“茶花”符号化、舞台的镜框式布局等形式对经典作品进行“解构”与“重构”,这种当代译法为歌剧艺术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依据。
三、新时代重庆音乐的话语论争与标识底线
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关乎具有中国艺术风格音乐体系的建构与“极优艺术”的生产。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围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这为新时代文艺发展建设明确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在世界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大格局中,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中,寻求极具价值引领、兼顾在地性与全局观的高质量音乐精品。
新时代重庆音乐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换等于音乐市场的繁荣或网络神曲的传唱。目前音乐界所存在空洞化的旋律、媚俗的歌词等部分现象,是脱离了音乐对“诗性”审美追求的结果。当然,这种反抗并非对抖音神曲等现象频发所带来的“人人都能搞音乐”这一判断的全盘否定。我们“既不能高估现有的网络‘神曲’所蕴含的某种生产力的解放,但也不能低估‘人人都能搞音乐’所带有的革新性”,而是要反思普通人对音乐的情感及音乐反作用于普通人的价值所在,并从音乐所处的艺术体制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中,去探究音乐在互联网时代生产与流通的基本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音乐界需达成共识的是,音乐并非体现优越感的文化权利机器,若所谓精美包装、曲调复杂、歌词高深的“好音乐”无法引发听众精神共鸣,无法表达民众“真心实意的情与爱”,这是否能视为好作品?将传唱度高的“口水音乐”(如抖音神曲)圈入自己偏见所筑成的审美牢笼中,这是审美谬误还是审美底线?面对重庆音乐产业的差异化发展,不能将作品简单归咎于歌词或曲风等内容形式的空洞化,而是要依据文艺自身属性,找准重庆在文化高质量发展中的获益底线、贡献底线;关注重庆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力底线;提高重庆文化软实力的域外影响力底线。
当然,这种底线追求只是作品质量保障的外在要求,更为关键的是,音乐家本人要怀揣审美情怀、释放审美个性、涤除思想杂念,“把创作作为毕生专注的事业,克服一切杂念,排除一切干扰,静下心来,把主要经历和思想集中到创作上来”。这是音乐创作者想要创作出经典作品的首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针对文艺领域存在的“浮躁”“迷失”现象指出:“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新时代音乐往往需要更好地引领全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方向,这就要求音乐创作不应抹去“人民色彩”。无论是影视配乐、交响曲,还是歌剧、流行音乐,新时代的音乐创作要关注以“人”为本的话语构建,与时代面貌、审美情怀、民族精神紧密联系,也要重视谱曲上是否是人民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从而生成集审美性、大众性、时代性、本土性于一体的音乐精品。如《一江清水向东流》(民族歌剧)、《幺妹拽》(歌曲)等,是重庆音乐在创新实践方面所作的积极尝试。
音乐这一听觉媒介重构了声音生态的时空秩序,更是依托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发展,与其他媒介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也就要求跨媒介语境下,音乐创作人要与时俱进,熟于数字技术使用,精于音乐媒介特性,聚焦“极优艺术”生产,进而完成具有时代气象、重庆标识及中国特色的音乐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的建构,为新时代重庆乃至中国的音乐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努力。
林弥忠,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访问学者,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舞台评论专委会委员。
于昊旻,毕业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现供职于重庆市美术家协会。
(重庆市文联《重庆文艺》编辑部供稿)